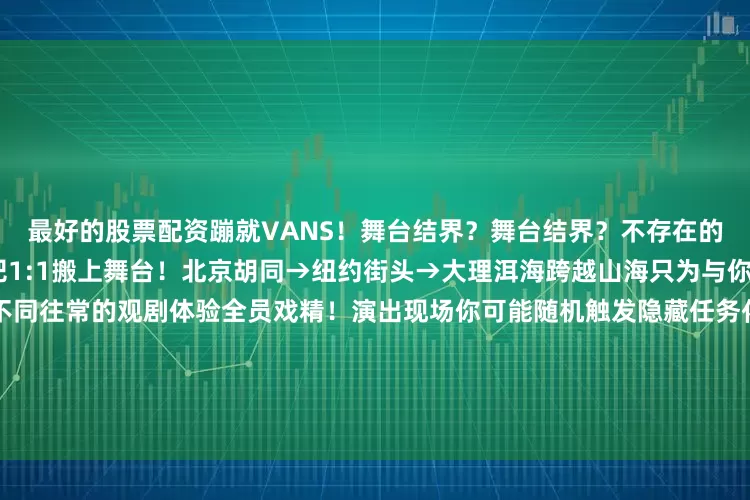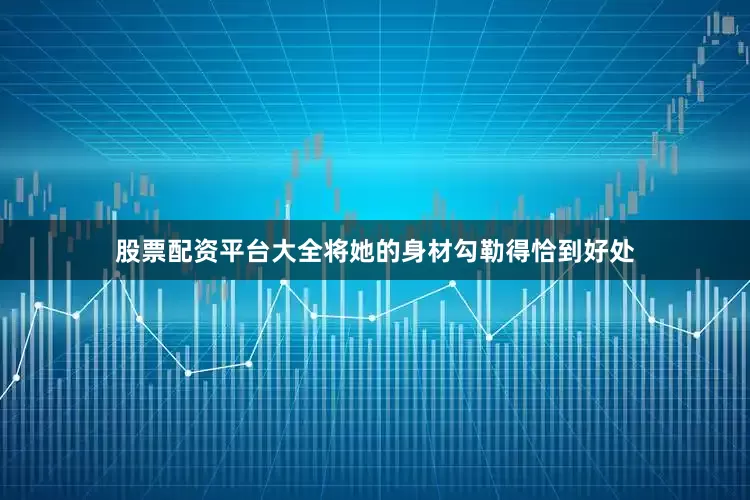马斯克近期在一次对话中的表述,引发了超出科技范畴的广泛讨论。他与乔·罗根及黄仁勋交流时提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高度发展,终将使得货币概念逐渐淡化,贫困得以消除,而工作也将从一种必需转变为一种选择。

马斯克的这番描述,竟遥远地呼应了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图景:在生产力极度发达的阶段,劳动将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马斯克以“在自家花园种菜”为例,阐释未来工作的自愿性与乐趣导向,这与马克思关于在高级社会形态中,人类将在摆脱了物质匮乏和强制分工后,实现自由、创造性劳动的论述,存在有趣的表象契合。两者都指向一个由高度自动化解放人类、物质极大丰富的未来假设。

然而,这种契合更多停留在对“结果状态”的描绘上,两者的哲学基础、实现路径与对“人”的理解存在本质差异。马克思的论述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形态的演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他所展望的“自由王国”,建立在彻底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消除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但社会关系的革命性重构才是关键。
相比之下,马斯克的预言更倾向于一种技术决定论的乐观推演。其逻辑是:极致的生产力发展将自然溢出足够多的财富,使得“全民基本收入”成为可能,从而消解经济稀缺性。
这一路径默认了现有资本主义框架的延续与自我改良能力,并未触及所有制和权力结构的根本问题。因此,尽管终点描述相似,但二者行走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马斯克预言货币将因极度丰裕而“无关紧要”。这一激进设想触及了当前经济体系的核心,即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即便在技术层面实现物质的近乎零边际成本生产,其分配机制仍将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若生产资料仍高度集中,技术红利如何确保普惠而非加剧垄断?若货币消亡,何种新的凭证或信用体系将界定获取商品与服务的权利?这些问题,技术本身无法自动给出答案。
历史上,技术进步往往首先扩大而非缩小不平等,因为它初始的控制权与收益权常归属于资本与少数技术精英。

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在现有体系下可能首先表现为企业利润的激增与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而非立即惠及全体劳动者。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资本市场对AI概念的狂欢,与对“工作被取代”的普遍焦虑并存,恰恰反映了技术演进与社会制度适配之间的深刻张力。将AI视为单纯“消灭”资本主义或某种制度的“铲子”,可能过于简化。
更现实的图景是,它将作为一个超级变量,剧烈冲击现有的就业结构、财富分配模式和国际力量平衡,迫使所有社会体系进行深度调整与变革。只有更好地驾驭这次技术浪潮、并解决其带来的社会公平、伦理治理等挑战的文明,才能赢得未来。

关于国家、民族形态演变的“白日梦”,则指向了技术冲击下文化认同的可能走向。若物质生产不再是人力的核心投入领域,文化创造、精神追求与社群归属感的重要性或将空前凸显。这可能导致文化身份更加多元和强化,但也对跨文化理解与共处提出了更高要求。
至于“机器人文明循环”的科幻构思,则是一个迷人的思想实验,它隐喻了技术、意识、文明传承与自我认知的永恒命题,这本身就是人类面对技术巨变时,试图理解自身位置的一种哲学性投射。

马斯克的言论之所以引人深思,不在于他“重新发现”了某个理论,而在于它表明,即使是最前沿的科技巨擘,在思考技术的终极社会影响时,也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那些关于人类解放、自由与平等的基本命题。这些命题已被人类最深刻的思想家探讨了数个世纪。
人工智能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迈向一个更丰裕、更自由社会的潜在技术路径,这让我们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接近实现某些宏大愿景的物质条件门槛。
然而,技术只提供了“可能”,而将“可能”转化为“现实”,取决于我们如何构建与之匹配的社会治理、经济制度和价值伦理。
这是一场远比技术研发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最终,定义未来社会形态的,不仅是算法的力量,更是人类集体的智慧、勇气与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
恒运资本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